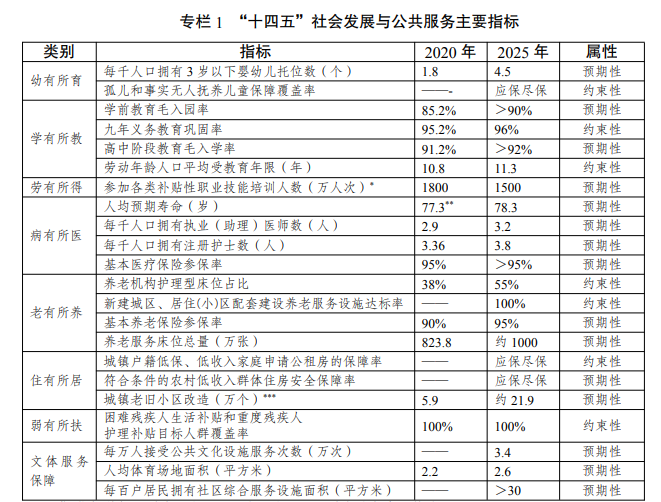雨和雨,不尽相同。在我记忆里,有一场雨,专属一个人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我38岁那年夏天,从郊区调到浦东新区工作,每天开车上下班。从家里开到新的单位,至少一小时。
第一天去浦东上班,就遭遇了一场暴雨。
照理说,上海的夏天,早上六点,天色应已大亮。因遇强对流天气,乌云底下的世界,如同黑夜。只有在雷电的瞬间,天地之间才会裂开一隙白天的样子。
汽车大灯照见远处红雨伞的那刻,我条件反射,摁了一下嗽叭。前方,有一个撑红雨伞的人,站在清晨六点的大雨里。雷电闪处,像一个闪烁的抖音符号。
近了,我看到那个撑着红伞的人,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雨衣,红与黄的搭配,经汽车灯光的渲染,令人联想起交通信号灯。又想,撑雨伞的人同时又穿着雨衣,估计是因为雨太大了,单靠一柄雨伞根本挡不住,才又加穿了雨衣。再靠近一点,我发现那是一件骑车人穿的雨披,雨披里的人正向我招手。
雨越下越大,挡风玻璃上的一双雨刮器,如同急流中迅划的船桨,前脚刚刮去一层雨,后脚的雨瞬间又卷水重来,一层比一层汹涌。雨刮器形同虚设。朦胧间,我感觉这里应该是老家的地域了,那个向我招手的人,莫非是故乡的某个熟人?莫非他认出了我的车牌号?
雨实在是太大了,水泥公路的路面,早有约摸20公分的积水。我将车停靠在撑伞人旁边时,车子掀起一拨雨浪,扑湿了撑伞人的裤管。
那个人走过来,靠近我副驾驶座右侧的窗玻璃,从雨披里伸出右手,轻轻地敲打车窗的玻璃。那张被雨披包裹着的熟悉的脸,就贴在流淌着雨水的车窗玻璃上,露出一口混浊牙齿,冲我傻笑。
那一刻,我整个人都静止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什么是她?那么早,冒这么大的雨,还顶着隆隆的雷电。
那个撑着红伞穿着黄色雨披的人,不是别人,正是我母亲。母亲脱下雨披,把它和红伞一起扔在雨里,打开车门,一头钻入我的车内,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上,又重重地关上车门,把哗哗大雨关在门外。
“妈,你这么早站在马路边做什么?是不是要去走亲戚?我可以送你。”母亲没有回答,她的左手拉起我的右手,侧着脸久久地看着我,傻傻地笑着。过了好一会,她才平静地说:“妈想你了,想来看看你。”她从汽车中控台的纸盒里,抽出一张纸巾,边擦着脸上的雨边说,“你调了新的工作,要去浦东上班。一个新驾驶员,每天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,妈担心着呢,想对你说,小心开车,不要开快车,安全第一。妈在这里等你,是你爸说的,这个路口,是你上班的必经之地。”
母亲抬了抬身子,解下搭肩背着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说:“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大肉粽子,是妈亲手摘的芦箬,亲手裹的,还热着呢,一会到了单位,还可以当早饭吃,还可以分点给你的同事们吃。”她像小时候那样拢了拢我的头发,“好了,不多说了,你去上班吧,记住,你是新驾驶员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母亲离开汽车的时候,我看见了她大腿以下的裤子、鞋袜全湿透了。我说:“妈,这么大的雨,我送你回家吧。”母亲说:“千万别送,再过一会,你姑姑夜班回家,她有车,会捎上我的。你快去,第一天上班,别迟到了。”
关掉了双跳灯,汽车缓缓启动。从后视镜里,我看着那个撑着红雨伞的人,正朝汽车的背影挥动着手,像一个缓缓变小的符号,终于淹没在大雨里。
这场大雨,伴着后视镜里那个挥之不去缓缓变小的身影,长了脚似地,一直跟我到单位的停车场。这场大雨,和那些夹杂着雨声的熟悉乡音一起,长了脚似地,一直跟随着我,如磅礴母爱,给我力量,伴我一生。
“转载请注明出处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