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天,山河田野中的新鲜食材争相露头,我倍加怀念那启蒙我味觉审美的第一条鳜鱼。
桃红李白,惠风和畅,时蔬郁郁清嘉。倘若春雨初歇,落花无意,池里的鱼儿也会耐不住寂寞,奋然跃出水面,激起层层涟漪。
三月中旬与朋友去杭州临平采风,在农家饭店吃了一盘油焖笋,无筋无渣,鲜香无比。老板说,这黄泥拱是一大早从山上挖来的。不过我们点的一盘咸菜土步鱼有点遗憾,土步鱼过于迷你,长不及三寸,只能从鱼汤中意会一下了。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杭州人口中的土步鱼即为塘鳢鱼,头大眼小鳞细,脑壳坚硬,体呈紫黑,间以黄黑斑点,相貌凶猛。三五条塘鳢鱼,浓墨勾勒,淡墨渲染,再配一枝斜旁逸出的桃花,就是一堂春色。
上海人也是塘鳢鱼的忠粉,小菜场偶尔也有,如今卖到150元一斤。家常做法是红烧,加点雪里蕻咸菜;或者与笋片、豆腐共煮,汤色乳白,其味不输河豚。
我在苏州吴江宾馆吃过一款糟熘塘片,舌尖一接触嫩滑鲜美的鱼肉,不由得微微颤动起来,滑入喉咙时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
桃花流水鳜鱼肥。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将江南的美定格在桃花、白鹭和鳜鱼上了,所以全家老小分享一条清蒸鳜鱼也是上海人打开春天的模式。当然,外脆里松酸甜口的松鼠鳜鱼更讨人喜欢,而瓜姜鳜鱼丝一直是厨师考级实操的一道坎。
近年来我对清蒸鳜鱼甚至火夹鳜鱼兴趣不大,也许是水产养殖的规模扩大,导致了鱼肉鲜嫩度的下降。在扼腕叹息时,我倍加怀念启蒙我味觉审美的第一条鳜鱼。
那是在我总角之年,跟妈妈回到故乡绍兴探望缠绵病榻的祖父,沈家老台门的最后一进便是我们家。门外有一条河,一座梁式石桥,老台门里的三公公经常在桥下钓虾,就像丰子恺在《吃酒》一文中写到的钓虾人,晚上他用小半碗盐水虾过半斤老酒。他的孙女比我大四岁,已读小学三年级,红扑扑的鹅蛋脸略显粗糙,农活和家务都能帮上手了。有一天艳阳高照,小姐姐在院子里支起三根短竹竿,搁了一张竹匾晒陈年谷子。她爹是大队会计,接到通知去公社开两天半会,按规定要交三斤谷子充当伙食。小姐姐说得自然平淡,在我眼里却是新事物。
为提防麻雀来吃谷,她就坐在屋檐下看守,又拖住我讲鬼故事。光天白日的鬼故事呒啥吓人,再加上小姐姐噱头不足,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,起身去逗弄小鸡小鸭,冷不防一只黄鼠狼从柴堆里蹿出,吓得我仰面跌倒,连带着将竹匾掀翻,金灿灿的谷子撒了一地。将落进石板缝里的谷子挑出来,可要费一番手脚啦。好,七大姨八大姑都来责备我,妈妈也来了,不由分说一顿打,我很配合,夸张地干啕,小姐姐满脸通红低下了头。
当天傍晚,三公公推开我家大门,提来一条正在扇动鳃帮子的鳜鱼:“我平常只钓虾不钓鱼,今天怪了,它自己咬了钩,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喏,给大生哥(大生是我爷爷的乳名)补补身体。”又摸摸我的屁股,“今天闯祸哉,哈哈,明朝给你拗只钩子,一道去钓虾好不好?”我看妈妈,不敢答应。当晚妈妈葱结姜片地蒸了这条鱼,夹了一条背脊肉给我吃,想不到鳜鱼的肉质这么细腻而且鲜美!而此前我只吃带鱼,连鲫鱼也认为刺多而不敢下嘴。
几天后我跟妈妈去镇上买东西,看到河边有人用草绳系着两条刚出水的鳜鱼,但无人问价。关帝庙前倒有一株桃花开得正艳,树下有个男人摆起地摊,糙米饭装在小钵斗里,饭尖顶着一撮霉干菜,几个路人就这么站着狼吞虎咽。等我长大后才知道,那一年,江南农村正从最困难的光景中走出来。(沈嘉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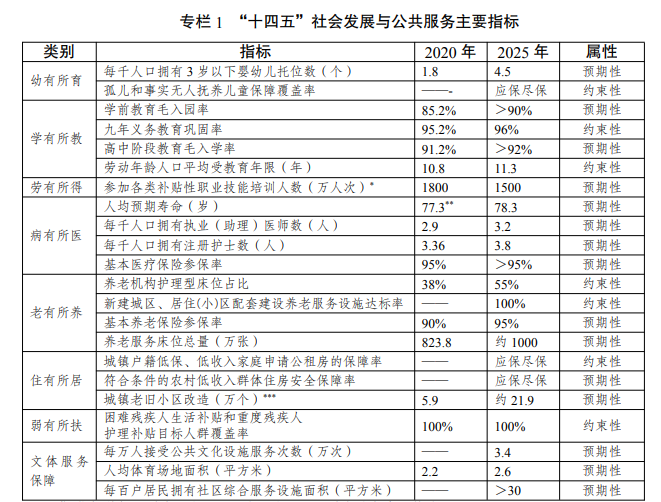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![全球热消息:[随心所欲汉化组]2.5次元的推荐成为了同班同学!?](http://img.kaijiage.com/2022/0610/20220610025523481.jpg)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