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隔三年,在中国名气颇高的导演新海诚,带着其新作《铃芽之旅》出现在内地银幕上,影片正在热映,并且以势如破竹的态势,仅用一个周末的时间,至截稿前票房已达到3.5亿。影片讲述了生活在日本九州田舍的17岁少女铃芽遇见了为了寻找“门”而踏上旅途的青年草太。追随着“闭门师”草太的脚步,两人一起去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冒险故事。和新海诚前作《你的名字。》和《天气之子》类似,《铃芽之旅》也把对东日本大地震的思考置入了故事里。
新海诚在这部电影中打开了自己,向社会关怀维度的艺术创作靠拢,以公路片的模式架构起自己的想法,把对日本311震灾的追思,以及后疫情时代危机愈发严重的日本社会、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放入了其中。新海诚告诉记者,这样的变化是他不曾想象过的:“在我的早期,我描写的是不服气,我自己处于一种不沟通的状态,因为早期我没有什么与观众沟通的经验,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描绘自己不理解的东西。而现在,我继续着艺术创作,并逐渐能与观众交流感情和思想,我想,我是花了20年时间才达到如今这个目的,如今这番改变。”
以下是新海诚谈及《铃芽之旅》与自我思考的记录: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新京报:你以往的故事一般围绕两个地点展开,一是东京,二是乡下。《铃芽之旅》中主人公却在日本各地旅行,在停留的地方采取行动,这可以被看作是新海诚作品的新发展吗?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?
新海诚:主角铃芽在日本各地走动,主要原因是我想拍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。在地方,人们会为死去的人举行葬礼,但当一个城镇、一个地方消失时却没有这种仪式。当我想到拍一部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电影的可能性时,我意识到为了访问一个地方,我需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,所以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关于旅行的故事,自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各地,这就导致了该片成为公路电影的形式。
新京报:铃芽见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,通过他们接触了当地文化,如方言、食物、习俗、歌曲,这些接触对铃芽来说意味着什么?
新海诚:这是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,在充实故事上,我思考了铃芽会有怎样的文化体验。早前我对宫崎骏的《魔女宅急便》有很深的印象,这也对我的故事有所影响,《魔女宅急便》在少女训练成为女巫的过程中,琪琪遇到了很多人,包括乌露丝拉和索娜。正如许多人指出的,琪琪遇到的女人体现了她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。我希望《铃芽之旅》是一个关于铃芽与女性们相遇的故事,我试图让铃芽在每个地方遇到的人都很有特色,是我以前从未描绘过的人物,比如在家里招待所帮忙的女孩和小吃店的妈妈,这些女性充当了铃芽与未知文化接触的催化剂。
新京报:描写灾害的电影,从《你的名字。》到《铃芽之旅》,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?
新海诚:回顾我自己的资质和历程,我不认为自己是会拍如同《铃芽之旅》这样的电影的。在我开始制作动画的时候,总认为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做,需要把庞大的故事留给别人,也一直试图根据日常情感讲故事:比如你在车上或下车时的感觉,或者你进入便利店的那个瞬间。但正是我之前一直在做的基于日常情感的表达,与我在2011年因为地震受到巨大影响的混合,才创造了《你的名字。》。与很多观众见面后,我决定必须做一些事来回应 《你的名字。》。在那种心情下,我制作了《天气之子》,再到现在的《铃芽之旅》。看过这几部电影的观众,与他们见面、交流,无论积极或是消极,都是促使我拍摄这部《铃芽之旅》的原因。
新京报:在《你的名字。》里,宫水家族发挥了记忆装置的作用,以避免灾难代代相传,你对拍摄存档记忆,并将其传递到未来的电影的可能性有什么设想?
新海诚:我没想过,我的制作能持续五年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,我很庆幸在这个时候能拍一部让几代观众都看到的电影,并且我认为现在不拍那就太晚了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12岁的女儿看了《你的名字。》 哭得非常厉害,这是她第一次理解了电影的意义,她说电影很好,但她似乎很难将这部电影与东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。我认为她不可能把这场灾难想象成千年一遇的彗星撞击的隐喻,对她来说这场灾难是与她这一代人无关的事件。随着时间流逝,他们与灾难间的距离将变得更遥远,但我认为世界上是应该有像铃芽这样有所记忆的人。铃芽和我女儿在年龄上相差不大,如果我们能通过以娱乐的形式创作像《铃芽之旅》一样的故事,使青少年观众与12年前的世界保持联系,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能做到的、有巨大意义的大工程。
新京报:“三部曲”的共同点是,儿童参与了纠正世界扭曲和拯救世界的行动,你在其中委托给孩子们的想法是什么?
新海诚:我认为孩子们能更生动、更形象地感受到这个世界,无论痛苦、快乐、颜色还是气味,孩子们对事物的感觉远比成年人强烈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儿童总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,也许正是这样的感觉吸引了我拍电影。
新京报:将严肃的主题和娱乐元素结合很重要,你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?
新海诚:当我决定处理“东日本大地震”这个剧情时,如果不把它变成一部具有娱乐性的电影就没有意义。这部电影在某些场景中必须有趣,而且在整体上必须有娱乐性。如果真正的悲剧在背景中,但人们说它不应该处理得娱乐,或者说它是不恰当的,那这莫过于电影最大的悲剧。虽然这部电影是虚构的作品,但我的目标是让它成为真实事件、真实情感的交流,所以影片结尾有一个场景是铃芽对一个角色说些话。我认为这些话本身并不是虚假,也不是超自然的现象,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。
新京报:感觉那个场景中发生的情感交流,是我们日常也会做的事情?
新海诚:就像那场戏一样,我有时候想告诉他们,没关系,他们可以长大,或者告诉他们即使现在很艰难,几年后他们可能也会微笑。如果借鉴我的个人经验,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。在《秒速五厘米》中,当我让明里说“我相信贵树君将来会好起来的”,我是在自言自语;《天气之子》中当我说“我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”时,我也在自言自语。我相信铃芽会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传达给观众,如果他们能理解想要传达的信息,我就非常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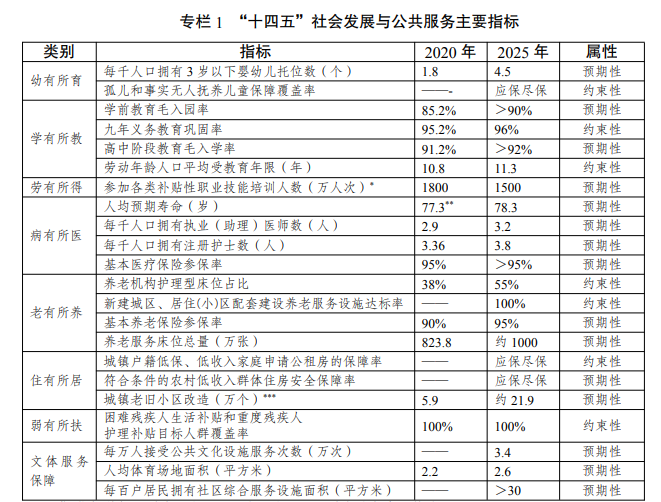





![[快讯]中国石油公布2022年年度分红方案](http://img.xhyb.net.cn/2022/0923/20220923104608741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